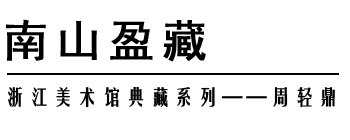周轻鼎(1896—1984),湖南省安仁县人,现代雕塑家,我国动物瓷雕的奠基者。24岁考入上海美术专科学校,后东渡日本留学,继而前往法国勤工俭学,先在巴黎高等美术学院雕塑系罗丹的学生让•布舍门下学习雕塑,再到里昂专门学习动物雕塑,并在法国学习、生活、工作达15年。1945年12月回国,任杭州国立艺术专科学校雕塑系主任、教授。新中国成立后任浙江美术学院雕塑系主任(后改任民间美术系主任),致力于动物雕塑的研究、创作和教学,取得了引人瞩目的成就。他承继法国写实雕塑传统,重视师法自然,注重表现动物生命力,力求形神兼具,不尚藻饰,语言洗练、生动,饶有情趣,富有诗情画意。
2007年12月,时在筹建中的浙江美术馆经多次与周轻鼎先生家属接洽,达成征集意向,征集周轻鼎自上世纪50年至80年代的动物雕塑作品200件,这批作品全面反映了周轻鼎风格形成的轨迹和艺术成就,为浙江美术馆征集首批较大规模艺术家捐赠项目之一。
-
1896年
公元1896年(农历丙申年四月初一),出生于湖南省安仁县。乳 名黄庭,号宅西,字显伦。排行第三,上有一兄一姐,下有二妹 一弟。父亲为前清拔贡,“周轻鼎”系其取之于“(周)定 王使王孙满劳楚子,楚子问鼎之大小轻重焉”(《左传·宣 公三年》)。
-
1916年
在湖南安仁县蒙馆任教。
-
1920年
就读于上海美术专科学校。
-
1929年
东渡日本,就读于日本东京川端画校。
-
1931年
赴法国,先就读于巴黎高等美术学校,师从让·布舍学 习人物雕塑,后又到里昂师从约翰·曼诺研习动物雕塑。作品多 次在沙龙获奖。参与发起成立法国中国留学生艺术研究会。
-
1945年
由欧洲回国。即任国立艺术专科学校雕塑系系主任、教 授。在国内雕塑教学中创立雕塑创作课程,开创先河。
-
1946年
1946年,领国立艺术专科学校复员北路(因抗战南迁,先至诸 暨、贵溪、沅陵,后又到贵阳、昆明、松林岗,最后至重庆沙坪 坝盘溪。抗战胜利后迁回杭州外西湖)返校途中不辞辛劳,一路 日夜穿梭,照看师生疲惫不堪,终在路经洛阳时不慎跌落车下, 严重伤及腰部,在洛阳住院三个月治疗。
-
1948年
解放前夕,为保全学校公有财产和保护师生的安全被公 推为教授会主席、校务委员会主任代行校长职权,并一方面与时任浙江大学校长的竺可桢一起前往南京募款,筹得经费以维持全 校日常开支及师生生计;另一方面通过积极组织师生义卖自救, 得以顺利度过难关,受到广大师生的敬重。
-
1949年
创作《八口之家》、《流民图》。
-
1953年
上海中苏友好大厦雕塑创作,代表作品有《俄罗斯 老农》。
-
1956年
在江西景德镇创作动物雕塑。
-
1958年
任浙江美术学院民间美术系系主任。
-
1959年
在浙江美术学院举办“周轻鼎动物雕塑展”。
-
1960年
在浙江龙泉创作动物雕塑。
-
1961年
在上海动物园创作室外大型群雕《大熊猫》。先后在上 海动物园、上海美术馆举办新中国第一次个人动物雕塑大型 展览。
-
1962年
受邀在北京建筑艺术雕塑工厂、北京工艺美术学校讲 学。专辑《动物雕塑》由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
-
1963年
在江苏宜兴美陶厂、浙江龙泉瓷厂创作动物雕塑陶瓷。 任第三届浙江省政协委员(之后一直连任至逝世)。
-
1964年
创作并完成杭州孤山《群鹿》大型室外雕塑。
-
1965年
在上海动物园写生创作。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完成《周 轻鼎动物雕塑》摄制、制作。
-
1966年
“文革”中受到严重冲击。
-
1969年
在绍兴参与《收租院》雕塑的复制工程。
-
1971年
在浙江博物馆“从猿到人展览”创作雕塑展品。应中国 科学院古脊椎与古人类研究所之邀,在北京指导古动物复原工作 (古代恐龙、剑齿虎等)。
-
1972年
再次应中国科学院古脊椎与古人类研究所之邀赴京并制 作《北京猿人》、《山顶洞人》浮雕等。
-
1973年
在苏州瓷厂研究创作。
-
1974年
在上海土畜产进出口公司研究创作出口裘皮动物。
-
1975年
在兰溪陶厂创作,并率领中国科学院古脊椎与古人类研 究所及山东师训班学生进行教学实习。
-
1976年
《中国大百科全书》收入辞条。
-
1977年
在杭州动物园创作室外雕塑《大熊猫》、《群鹤》。
-
1978年
在上海动物园创作室外雕塑《群鹿》。在温州举办工艺 美术讲座。
-
1979年
受邀在南京艺术学院讲学。在丽水举办雕塑讲学。
-
1980年
在常州讲学。向中国美术馆捐赠作品二十四件。与北京 等地教授在陶都江苏宜兴丁蜀镇研制陶瓷新品( 《人民日 报》专题报道)。
-
1981年
在湖南郴州、桂阳、长沙等地创作并讲学。为中国美术 学院雕塑系作专题讲座。在郴州创作大型室外雕塑《大象群》、 《大熊猫》。
-
1982年
中央新闻电影制片厂的《周轻鼎的动物雕塑》摄制完 成。在龙泉瓷厂研究创作。上海雕塑界同仁张充仁等为其举办庆 寿活动。在宁波创作《梅花鹿》、《大熊猫》等室外雕塑。
-
1983年
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周轻鼎动物雕塑选》。在衡 阳创作回雁峰室外大型雕塑。
-
1984年
在杭州大观山创作室外动物雕塑。11月22日19时45分 因病在杭州逝世。
文/周轻鼎
一
我这一生没有干出什么大事情,就是做一些动物雕塑,也可以说平凡得很。但我的生活道路是曲折的,我走过的道路,连我自已也是意想不到的。好象是画大写意画,有许多偶然的东西,有几笔是随随便便画出来的。我又好象是一本字典,一翻这本字典,就会了解近百年的典故来。
当我第一次离开家的时候,我只想到外面去看看世界是什么样的,根本没有想到会到日本、到法国去留学,也没有想到要当一个动物雕塑家,也没有想到要在美木学院当離塑教授。然而,这些毕竞是事实。在八十年来的漫长生活中,我曾经有过各种各样的追求,经受过失败的痛苦,也体验过成功的欢快;有曲折离奇的情节,也有动人心弦的镜头。如果有人要用我的生活素材拍电影,起码也可以拍三、五部。有时我回忆往事,虽然有些经历早已忘到九霄云外,一点也想不出来,可有些情节、话语、场面、特写镜头,历历在目。
我是湖商省安仁县人,生于1896年。安仁县是一个山区小县,你们大概听也没有听说过,反正我是一个从穷山沟里出来的人。我家那时有四口人:父亲、母亲、哥哥和我,我父亲是个秀才。我母亲是一个家庭妇女,不识字,但很聪明,过年过节时会用米粉团子做各种动物,我哥哥是家里的主要劳动力。当时科举制度已经度掉了,外地大概已经兴办了洋学堂,但在我们那里还只有私塾。私塾分初、高两级。初级相当于现在的小学和初中,高级相等于现在的高中,我父亲在一个高一级的私塾里教书。我上的那个学校是我们地方的唯一的学校,离我家说有三十里路,其实至少有五十里。到学校去,要爬好几座山,学校的课程有语文、数学、体操。那时的语文课,实际上包括现在的历史、古文课,读的是四书五经、《古文观止》、《史记》等,也学作律诗。我在学校里学习成绩还不错,理解力强,记忆力较差,讲都讲得出来,背往往背不出来,我的语文老师和我的父亲认识。记得有一次,我父亲在家里对来作客的我的老师说:“我的儿子背不起来,他能背一半就不错了。”相反,我有一个堂兄弟,他的记忆力强,背工很好,但不大理解,不知什么时候,看到巴甫洛夫在一本书中说:“一个人的脑子里有经有纬,经管记忆,纬管理解。有些人经纬都很强,有些人片面发展,其中一方面比较强。”大概我的纬比较强吧。对于生理学,我连一知半解也谈不上,刚才是随便说说的。
我从小就喜爱艺术,所谓艺术,其实就是喜欢画中国传统的山水、花鸟画和捏泥人。每逢过年过节,我母亲总是用米粉团子捏各种各样的动物 ,我也学着捏。每逢假期,特别是暑假,我自已也用黄胶泥做各种动物玩。的确是玩玩的,不知道它叫动物雌塑。那时学校重视写字,我写过各种各样的贴。年龄稍大后,我开始临摹传统的中国花鸟山水画,所以后来能考取上海美专。
读书干什么?不晓得。我二十来岁时,就开始在一个地主家里教蒙馆了,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当家庭教师。教的是十来岁的小孩子,但内容也是“子日:‘学而时习之,......'”那一套。味道很差,比坐牢还难受。
这样的生活过不下去了。不知什么时候,我向自己提出了一些问题:世界有多大?外边的世界是怎么样的?我要到外边去闯一闯,看一看。有一天,我借故跑到家来了,想同我的父母商谈出门的事。
回到了家里,不敢把自己的打算对父亲讲,先对母亲说了。
“妈,我要出门!
“到哪里去?”
“到外边远的地方去。”
“去干什么?”
“去看看,看能不能找到比较好的工作。如果我能闯出一条路来,我一定把您也带出去。
“你想得倒美!”
有一天,妈妈终于把这件事对父亲讲了。
这天晩上,父亲把我叫去。他抽了一阵旱烟后,劈头就问:“听说你要到外边去了,我问你:到什么地方去?去干什么?什么时候回来?”
这三个问题,我一个也答不出来。我不知道外边有什么地方,只听说过长沙、上海、北京这些地名。去干什么,更是无从知道。我不知道世界上有多少工作好干。对第三个问题,我更是无法回答。对这三个问题,我都是回答:“不晓得!”
我这个人的性子是固执的,我父亲知道。再说,我在家里也没有多大用处,所以父亲就答应了我的要求,但说没有钱给我做路费。妈妈舍不得我走,但又管不住我,只得顺我的意,让我走。我和妈妈,东借西凑,总算搞到三个袁大头(三个银元)。
有一天,我终于背着个包袱走了,这时是二十四岁。
从此,我再也没有看到我的爸爸、妈妈。以后回想起来,心中总是一阵酸痛。
二
我是步行从家里到长沙的,一共走了八天。一到长沙就泻肚子,随便买一点治肠炎的药,一吃就好了。走遍了长沙街道,开了开眼界,心里又想:“到长沙不是我的目的,长沙算什么东西!我家乡的人也有在长沙的。我要到北京去!”走到了火车站,没有钱买票怎么办?混进去!心里想:“要抓就抓,要打就打,要骂就骂。反正我要到北京去。”终于混进了车站,上了开往北京的火车,那时一切都很混乱,到处都有空子好钻。査票的人有时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总算叫我混进了北京。
到了北京,我找到了湖南会馆。那时候讲同乡关系,一到外地,湖南人碰到湖南人,一讲话,就亲密起来。住在湖南会馆不化钱,吃饭要吃自己的,住了几天,钱快要花光了,心想,大概有两条路可走:一是当兵,吴佩孚正在招兵;二是考学。在街上看到许多大学的招生广告,这时大概是暑假,我想尝尝大学的味道,决定考学,到朝阳大学去报考上海美专。我父亲会画画、作诗、刻图章、写字,我也跟我父亲在这方面学了一些。那时考试很简便,当场画了一张画,大约是花鸟画。第三日,就通知我,说我被录取了。
从北京坐火车到天津,由天津坐“阜生号”轮船到上海。也是不买票,混进去的。来查票时,我躲到一堆天津大白菜里。査票的走了,我又大揺大摆地出来了。古语说,“穷则思变”。人一穷,胆子也大了。顶多不过打一顿,赶出轮船,怕什么!
到了上海,住到上海美专的宿舍里。校长是刘海粟,听说是比我大一岁。我交不起学费,总务处的个白胡子老头子跑到我的宿舍里来说:
“哪个叫周轻!费还没有交?”
“是我,我没有钱,等几天再交。”
我笑着对他说,态度挺好,他拿我没有办法。这是软功夫。我两个星期没交伙食费,但照样吃了饭。
我和一个同学混熟了。他住在一个亭子间里。有一天,他对我说:“你也到我的亭子间里去住吧,不要在字校里住,免得叫人家天天讨账。”于是我搬到那个同学的亭子间里去了。这个同学对我很好,给了我一些钱,交了学费。这个同学叫什么名字,现在已经记不得了,更不知道他在哪里,是否还在人世。我是对他是感激不尽的。古诗说,“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在生活中常常有这种情况。我居然到过长沙、北京、天津、上海,居然坐过火车、轮船,居然在上海美专上起学来了。
那是刘海粟先生来上课,穿着西装,满口艺术名词,我感到他很神气。我上的是师范科,什么都学一点,有中国画、西洋画、劳作。
我到北京时,第一次看到了自来水,龙头一拧,水哗哗地从管子里流出来,要多少有多少!我从北京写信把这件事告诉我父亲,父亲来信说:“世界上还有这样的事呀!”我在长沙第一次看到外国人骑自行车,感到不可思议!
在上海美专,我学习很用功,因为穷,所以拚命学。一个姓马的老师待我很好,认为我有出息,画得好。有一次他把我画的画拿给全班同学看,有时叫我教其他同学。
当时曾做了一首诗,现在还记得:
那甘株守困英年,
赤手空拳猛着鞭。
目睹疮痍几遍地,
心怀抱负可齐天。
断粮岂敢穷途哭,
辍学权归破庙眠。
多少男儿坚志气,
始终不畏苦酸煎。
这首诗大概是在从天津到上海的轮船上写的。
我进上海美专那年,大约是一九二二年。在上海美专学了两年。我这个人总是不安于现状,总想往高处走。上了美专,还想出国留学。一九二四年,我终于找到了个机会到日本国东京去了。想开开洋荤啊!
三
当时,人们崇洋的思想比较严重,说是到日本留学是“镀银子”,到西洋留学是“镀金子”。我也受了崇洋思想的影响,那时要到日本去,也是为了镀银子,认为在外国喝一口风,回来也会吃香。当时,有钱的人才能留学,在日本留学的大都是富僚、政客、大资本家、大地主的弟子。留学是他们升官发财的道路。对留学,穷人连作梦也不改想。我到日本去,也是靠钻空子。我到了东京,进入“川端画校”。在东京认识了一些中国华侨,其中包括那时在东京开饭馆的我后来的岳父,也就是现在的老伴林桂松(我平常叫她明三)的父亲。我的岳父有爱国思想,中国在日本东京的倾向革命的爱国人士经常到我岳父的饭馆里聚会。但也有一些有钱的官僚子弟到那里去吃饭。官僚子弟看到我们这些穷留学生,经常表现出看不起的样子,有时竞说:“你们有什么资格到日本来留学?衣服穿得乱七八糟!丢中国人的脸!”实际,丢人的正是他们这些对日本当局百依百顺的人。
日本人很看不起中国人。有些中国人也看不起中国人,见了面不能问:“你是中国人吗?”被这样问的人是不高兴的。
在东京,中国和日本的关系很紧张。我因说了日本侵略中国的话,被日本人听到了,传说要捉我,我不得不离开日本。那时我和我的老伴刚刚结婚两个月,我就不得不离开了她,一去就是二十!
到那里去?回中国吗?到欧洲去吗?还是决定到法国巴黎去。那时正好有一只轮船开往巴黎,我就通过关系,乘船到巴黎去了。
通过在巴黎的中国留学生的介绍我进入了巴黎高等美术学院。
四
巴黎美术学院雕塑系有两个著名的老师,一个是米格罗斯,一个是让•布舍。我和刘开渠先生同在布舍工作室学习,刘先生先进布合工作室。程曼叔先生在米格罗斯的工作室学习。米格罗斯的雕塑象是一朵花,讲究美丽。布含的雕塑是讲究“意到笔不到”,泥巴一加,拖拖就好了,不必精雕细刻。我是三十多岁才学雕塑的。记得现在在北京中央美术学院教雕塑的滑田友也在布舍工作室学习,他比我去得早。
我在巴黎学习、生活十五年,可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最苦,刚进美术学院,人生地不熟,不懂法文,一边学习,一边做苦工。第二个阶段,稍微好一些,认识的人多了,法国话也基本上听懂,也会讲几句了,赚钱的办法也多了。第三个阶段,有了固定的工作,生活好了一些。
先说第一阶段。晚上睡在床上时。经常想:明天早上的面包钱还不知道在哪里?每逢星期天,人家都快快活活地逛公园,参观博物馆去了,而我则是到人家家里去找苦工做。主要是给有钱人家擦地板,先用一团细丝把地板上脏的东西擦掉,然后打蜡,最后用布擦光。有时,到私人的苹果园去帮助翻土、整枝。我小时候在家里也是经常参加劳动的,我的手指捏锄头捏多了,手指都变成向一边弯曲的了。在巴黎时,有个同学看到我的手指时说:“如果列宁看到你的手,一定马上给你分配一个工作,你是劳动人民呀!”
后来,我找到了一个好的赚钱门路——卖豆腐。我因为在法国卖过豆腐,所以你们同学暗地里称我为“豆腐教授”。你们当我不知道?其实我老早知道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中国人是做后動工作的。有些士兵在战后留在法国了,中国饭店需要豆腐,他们就做豆腐。豆腐是中国的特产,法国人只会吃,不会做。我每天早上一起床,就骑个自行车到豆腐店去把做好的豆腐运到几家中国饭店去,或者运到喜欢吃豆腐的人家家里去。后来我又在好几个地方设了卖豆腐的点。著名音乐家冼星海同志有一年就来帮助我推销过豆腐。下边再细谈。
巴黎车子很多,小骑车总是来往不断。有同学对我说:“你不要这样干了,车子这么多,你骑脚踏车,又带这么重的东西,碰到汽车怎么办?这个事情不好干呀!碰到车子,真是性命也没有了。”我说:“不怕,一个人被逼得无路走时,就不怕死了。”我不是愿意在巴黎卖豆腐,可是不卖没有饭吃啊!结果,有一次还是被车了撞倒了。还好,没有出大问题,只是在医院住了六个月。
讲起在巴黎卖豆腐,就会想到音乐家冼星海。起先,我曾和他住在一个院子里,后来,他搬到另一个地方去住了。他后来住的地方就成了我的一个推销点。我每天骑车子把一盘豆腐送给他,他替我卖掉。第二天再送豆腐时,他把前一天的盘子和卖豆腐的钱还给我。
几年过去了。有一次在鲁佛尔博物馆碰到了冼星海。我和他坐在一条长凳上,他说:“我要回国去了。”我心里想:“你给我卖豆腐卖这么久了,总要倒杯茶给你。”我在口袋里摸一摸,钱在口袋里。我就请他到一个大馆子里去吃了一顿,大概用了六个法朗。我又拿出五十个法郎给他,他起初不要,但看我很诚恳,在手里把法朗摸来摸去,收下了。他说:“你这五十个法朗比一百个法郎,比一千个法郎还多一些。”他回到上海后,给我写了一封信,说他在一个电影制片厂找到了一个工作(配乐)。后来,他到延安去了。他生了肺病,第三期,到莫斯科去就医,不幸去世于莫斯科。他比我小两岁。若现在还在,是八十岁了。
除了擦地板、买豆腐,还给同学们理发。我不要同学们的钱,但有些同学一定要给我一些东西。开始学理发时,没有对象,滑田友主动让我理。记得第一次给滑田友理发,理得长短不齐,使得他不戴帽子就不能出门去。他照了照镜子,无法不笑,说:“这个样子,叫我怎么好出去呀!”后来,在北京见了滑田友,我们就想起了那句话,不约而同地说:“这个样子,叫我怎么好出去呀!”
在这里插进去一个故事,也是与卖豆腐有关的。有一座大房子,我经常到那里去送豆腐。这座房子的大门里住一个大约是退休了的法国老太婆。当我每天把一盘盘豆腐送到这座房子里的订户手里时,经常把从豆腐里流下的水洒在院子里的地上。法国老太婆每次看到此种情景,都表示出非常讨厌的样子。有一次,当我走过的时候,她终于开口了:
“送豆腐的中国人,你能不能不要让水流到地上?”
我听了,回答说:“没有水,怎么能做出好吃的豆腐呢?”
我打算治治这个老太婆。下一次,我送豆腐的时候,多带了--盘豆腐,并在这盘豆腐里放上大量的辣椒粉。我准备把这盘放有辣椒粉的豆腐送给这个老太婆。
当我走到大门口的时候,我特地走到老太婆的家里,把一盘豆腐放在她的桌子上。我很客气地用法国话说:
“老太太,中国的豆腐好吃啊,这盘豆腐给您,不要钱!”
老太婆的脸上出现了满意的笑容。
当我下一次又去送豆腐时,老太婆见了我把我叫住了:
“可把我要辣坏了!你们中国的豆腐有什么好吃的?简直象吃辣椒!”
“是有点辣呀!你还不习惯,若是吃惯了,不吃还不行呢!越吃越有味道!”
后来,这老太婆再不讲我把豆腐里的水酒在院子里了。我也小心了一点。她见到我很客气,我把没有辣椒的好豆腐送给她几盘。后来,她也订我的豆腐了,结果我们简直交成了好朋友。你对我好,我也对你好,有来有往嘛!
到第二个阶段,我的生活比较好一点了。认识了不少人,朋友也多了。能帮助的人多了。会讲法国话了。在雕塑学习方面有了很大的进步。我早上都是起得很早,卖豆腐是在八点钟以前干的;到八点钟,我一定走到教室里,开始学习。
布舍老师有一次批评别的同学而专门表扬了我。我记得他说过:“你们看周轻鼎,在课外工作那样多,而在雕塑学习上又进步这样快!”在星期天,我经常替人家做装饰雕塑,有时还为农村做一些动物雕塑。做这些工作赚的钱,比卖豆腐好多了。
第三个阶段,我主要靠画传统的中国画和仿制传统的中国雕塑维持生活。嫌的钱更多了。我小时候跟父亲学过画,后来在上海美专学了两年,因此画山水、花鸟、古装人物(主要是仕女)都可以应付。
外地的普萨灵。我们中国人用毛笔画一些传统的、具有民族风格的东西,法国人拿去当室贝。有时在玻璃后边画画,还画一个假图章;有时在大盘子上用油画颜料画中国画。有个法国人,专门开一个店铺,请中国人去画,给一点工钱,老板大发洋财。我的雕塑基本功已经不错了,仿制起中国传统的雕塑形象来,得心应手,很方便。巴黎城里每一个区都有寄卖美术品的商店。中国的传统美术作品,销路很好,十八罗汉、八仙的销路更好。雕塑底座上都标有“中国制,原作”。其实都是粗略的复制品。一般卖三百法郎一件,抽税很高,大约抽10%。我做中国传统雕塑形象,赚的钱很多,不想回来了。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巴黎沦陷,我逃到里昂。在里昂有时帮助人家做大雕塑,有时做中国传统的小雕塑出卖。我在里昂住了五年,主要跟雕塑家杜马学雕塑。杜马是专做动物雕塑的,我有一件动物雕塑至今还放在杜马的花园里,他看我做的好,就叫我翻成水泥,放在花园门口。一九四五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中国战胜了日本,我想回国来工作。巴黎虽好,总是外国的地方。说不想回来(只是说赚的钱多)是假的,还是想念祖国啊!那时心想:抗战胜利了,要开始建设了,大家都会过和平幸福的新生活了,自己也该回国尽一份力了。回去在街头、广场做一些纪念碑,在公园做一些装饰雕刻,该多么好啊!
上次说过,我在日本结婚后两个月就离开了。我曾和我的岳父母通过信,知道他家早已从日本搬回福建老家了,我老伴林桂松一直等着我,还未改嫁。我要回国同爱人团聚了。
五
一九四五年十二月,我回到了祖国。先到重庆,很久找不到工作。一个和我一起回国的学飞机制造的工程技术人员,住在重庆磁器口,找不到工作,生活无着,自杀了,重庆的报上登有他自杀的消息。经过朋友的推荐,我总算找到了一个工作:在国立艺专雕塑系教雕塑,一去就当了雕塑系主任。一九四六年,国立艺专复员到杭州,我也跟着来了。
我非常失望。回国前,想得很好,想着回国来要大干一番。可是,看到中国抗战胜利后混乱的样子,心就凉了半截。在学校除了教雕塑外,没有雕塑好做。就是教雕塑,也不能由自己的意。国立艺专的校长,原来是潘天寿先生,后来(大约是一九四八年)国民党派来了汪日章,代替潘天寿,对国立艺专实行反动统治。当时,解放战争已经开始,学生运动风起云涌。浙大、艺专等校的进步、革命学生,一直在进行着反饥饿、反迫害的运动。我猜想艺专也有共产党员,但不知是谁。艺专的进步革命学生经常组织同学唱革命歌曲、演革命戏剧,刻具有革命内容的木刻。雕塑系的大部分同学搞创作时也塑造工、农、报童等劳动人民的形象。一四八年雕塑系毕业班创作时,有一天汪日章来到雕塑系教室,看到毕业班同学做《工人》、《农民》、《报童》、《播种者》(农村妇女)等形象,非常恼火,暴跳如雷。
“谁叫你们做工农的形象?这是什么意思?”汪日章质问毕业班的同学。
“是我们自己要做的。”同学们回答。
“去把周先生叫来!”
当我走到教室时,汪日章气势汹汹地说:“做工人、农民的形象,这不是要造反吗?出了问题谁负责?”
我当时也是气得要命,把汪日章顶了回去:“工人做工,农民种地,报童卖报,这是最平常的人物,为什么不可以做?”
“统统给我打掉!”汪日章命令说。
“要打,你自己去打吧,我打不下去!”
汪日章气呼呼地走掉了,结果他也并没有来打雕塑,大概只在他的黑名单上记了一笔,。
当伪国大开场前,我不知是吃了豹子胆怎么的,竞敢做了浮雕《八口之家》和圆雕草图《流民图》在一次展览会上展出。前一块浮雕表现的是一家农民八口人的悲惨遭遇。后一座圆雕草图表现的是劳动人民离乡背井、颠沛流离的场景。总之都是要给国民党反动统治下的人民生活画一张像。后一件作品在艺专陈列馆展出时,标题上还注有“献给国民代表大会”等字样。摸了一下老虎屁股,也没啥关系,国民党当局并未敢动我。
临解放时,汪日章跑掉了,学校处于无政府状态,教师们公推我为教授会主席、校务委员会常务理事。那时候,我的责任非常重大,很多事要做:解决全校师生的生活问题(曾和竺可桢一同赴南京讨取经费),维持学校的教学工作,办食堂,和进步同学一起搞迎接解放的工作。杭州解放时,国立艺专校产没有受到损失。接近解放时,国民党搞“应变”,进步革命同学也搞“应变”,利用“应变”这个名称,内容是不同的。我那时大概被推选为“应变会”主任,好象开过大会。其实,我是挂挂名的,具体搞工作的是进步的革命的同学,现在才知道,那时艺专的地下党领导了这一工作。
六
有一幕戏忘记说了,部就是一九四七年在抗州夫妻相会的情节。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后,通讯中断。我不知道林桂松一家留在日本还是回国了。抗日战争胜利后,我写了封信寄给林桂松福建老家,后来知道这封信林桂松收到了。她家已于抗日战争开始后迁回福建,他爸爸已在抗战期间去世。原来,桂松的妈妈、姐姐曾劝桂松改嫁,可是桂松不肯,一直在等着我。一九四七年,林桂松得知国立艺专迁回杭州后,一个人来找我。
当时,国立艺专在外西湖十八号,我住在学校后院的一座楼上,后来此楼作实用美术系的教室。有一天上午,门房老顾在楼下叫:“周先生,周先生!”我走出来问:“什么事?”老顾说:“有客人来看你,在传达室会客室。”我走到大门口会客室,把所有的客人扫视了一遍,看不到一个认识的人,而老顾又不知到哪里去了,所以我回到自己的寝室。过了半个钟头,老顾又到后边来叫我了:“周先生,你怎么搞的?客人等你半天了,你怎么不去会客呀!”我说:“我没有看到有什么客人。”老顾回答说:“那个女的就是找你的!”我赶紧跑到大门口会客室去。一看,确实有个女人坐在那里,脸朝窗外。我仔细看了看女人的侧面像,好象在哪儿见过。我走上前去问她:
“请问您是找哪一个的?”
“我找周轻鼎。”她国答。
“我就是周轻鼎!”
“我是明三!”
夫妻终于认出来了。我带她到后边楼上去了。她走进我的房间后,还没有坐下来,就用眼睛到处看,看看墙上、桌上的照片,看看床下有没有什么特别的东西。后来我才知道,她是要査看査看有没有女人生活过的迹象。当她看到相片中没有女人,桌子上没有女人的用品,床上没有女人或小孩的鞋子后,这才比较放心了。原来,她听别人说,我从法国回来时带回来了一个法国女人,而且已有一个孩子了。大概是人们“想当然”的吧!在吃午饭的时候,她还把她特地带来的银筷子拿出来用,把银筷子放在汤里搅一搅。后来知道,这是她临行前别人给她出的点子,说是法国女人的心是狠毒的,她知道你去,说不定会在菜汤里放毒药,你把这银筷子放在里面搅一搅,如果有毒,银筷子就会变黑。白从她用银筷子在菜汤里搅了一搅后,她才完全放心了。
那时候,我已年近半百了。一九五〇年,我到北京博物馆工作,她才生了一个孩子,是在协和医院生的,难产。这孩子就是现在的逢盛,意思是说我们是“躬逢盛世”。
良好的榜样——记动物雕塑家周轻鼎教授
文/张祥水
八十三岁高龄的周轻鼎教授去年来我院讲学两个月,我们同他朝夕相处,亲聆教诲,日睹他严肃认真的教学工作和精湛的技艺,深受感动,他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周教授是我国著名的老一辈雕塑家,曾留学日本、法国研习雕塑二十年,到过许多国家的博物院、动物园临摹和写生。回国后,他看到国内园林和公共场所没有动物雕塑,也没有这方面的专业工作者,就立志专攻动物雕塑。三十多年来,他坚持不懈地创作了数千件作品,获得了广泛的赞誉。
周老在我院两个月的教学工作中,做了许多指导学生的示范作品,给我们美的享受。他雕塑的动物形象,气韵生动,粗犷有力,具有鲜明的个性,无论是骏美的马,秀雅的鹤,还是率真淘气的熊猫,威武凶猛的狮虎,甚至笨拙又逗人的棕熊,无不栩栩如生,形神兼备。在他雕塑刀下的梅花鹿群,更是千姿百态,维妙维肖。作者着力刻划它们娇健的身躯、灵巧的四肢,突出它们驯良的眼神、警惕的耳朵和富于装饰性的高耸鹿角,使之各具神采而又富变化,耐人寻味。雕塑《斗羊》,还选择了一触即发的瞬间,把两只公羊全神贯注认真对敌的神态刻划得尤为生动。他以粗犷的手法配上山披的背景,烘托了紧张气氛,把羊的肌肉颤动和全身用力等动势,表现得淋漓尽致却又恰如其分。
周先生不仅擅长小型动物雕塑,他还曾创作许多成组的大型园林动物雕塑群,他在不少公园和动物园的大树荫下、水塘小岛或花坛中,塑造了成群的仙鹤翩翩起舞,花鹿悠闲走动,而熊貓则相互戏耍活泼淘气,其构图都别致生动,若隐若现,雅观宜人,在优美的自然景色中增添无限生趣。
其作品之具有如此强烈的感染力,与他一心扑在动物雕塑艺术上,长期细致地观察各种动物并反复实践分不开。他在教学中强调师法自然,要学生长期与动物打交道。他说,动物好动,不可能安静下来做你的模特儿,要刻划它们的特征、习性、表情,必须细致深入地长期观察记忆,满怀激情地经常写生,并不时用泥巴学会迅速抓住对象的生命,把它记录下来。只有对动物了解得深刻,同它们建立深厚的感情,才能使自己的作品真实生动面富于生命力。几十年来,周老就是以动物园为家,从不间断对各种动物进行观察、写生和创作。他在上海四郊公园就先后住了十年,无论是清晨、深夜或烈日当空,他总是细心分析研究各种动物的姿态活动和它们的精神变化。他经常说:“搞我们这一行是不能按办公时间上下班的”。正因他终年累月与动物打交道,所以他能对各种动物的习性、姿态了若指掌,能把它们动人的特点和美的神情在雕塑刀下得心应手地表现出来。 周老几十年的雕塑实践,还始终坚持在艺术创作中应有自己的特点。他对学生常说:“艺术家应象火焰一样,使自己的作品有热情,有生命,能激动人心”。他严格要求学生把动物的基本形体结钩做准,但又一再强调说,单做准轮廓,没有感情的贯注,就表达不出爱憎的情操,把雕塑做得面面俱到,不能表现其生命力,也难以引起观众的共鸣。因此,他主张抓形为了传神,要学生在轮廓准的基础上更注意神情的表现,要大家学会以少胜多的表现方法。他指出,创作要意在笔先、胸有成竹,就要对各种动物的个性与喜怒哀乐都能深入了解,不但要有深厚的雕塑基本功,也还要有各方面的素养,才能概括集中有所取舍和有所强调,达到言有尽而意无穷的神情并茂的艺术境界。
周老出于对动物雕塑的强烈事业心和责任感,年老不服老,不论酷暑严寒,除年复年地坚持教学和创作外,还不时远离家门到各地传授知识和技能,经常“送货上门”,不计报酬地为陶瓷厂指导工作。七九年暑假,他为浙江萧山瓷厂做了四十几个品种的动物雕整,亲自制作、修胚,直到一件件产品出窑,都一一过问,负责到底。他还不断为各地工艺部门办短训班,培养了大批创作设计的新生力量。这次来我院美术系讲学,第一天上课就对大家说:“我们这两个月学习等于一场战斗”。整整两个月,他始终严肃认真,一丝不苟,从朝到夜,把全部精力都倾注在教学上。通过临摹、写生、创作三个阶段,他指导的十七个同学,都能较系统地掌握了动物雕塑的技法,做了八百多件作品,平均每人多达五十件,同学们都反映周老师的教学,“听得懂,记得牢,时间短,收获大”。 童年时代的艰苦生活形成了周先生忠厚坚毅的性格和勤奋俭朴的生活习惯。他穿着朴实,粗茶淡饭,对物质生活从无奢求。他曾说:“我从湖南一个山坳出门求知,随身只带两块大洋和一个小包楸,步行到长沙,后来辗转到了北京、上海又出国。在法国靠勤工俭学维持最低的生活和支持上学费用。”由于历尽沧桑,他深知今天美满生活的来之不易,因而始终保持着勤劳朴素的劳动人民本色。为了跟同学朝夕相处,他竖决辞退了原已安排好的高级招待所,就在教室边找了一个小房间住下,一日三餐跟大家一样在食堂排队打饭,从不特殊。他每天清晨还亲自打扫走廊厕所,擦洗门窗,凡他所到之处,总是清洁整齐井井有条。他不单自己这样做,对我们师生,也同样严格要求。他常说:“我不光教做动物雕塑,还要教你们如何做人”。他认为,要学好雕塑,先要学会做人,首先是要确立一辈子用动物雕塑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学生掉了一块泥巴在地上,他就叫拾起来;教室不整洁,要学生打扫清爽再工作。若讲了不见效,他默默无声地亲自动手,用自己的行动教育大家。真可以说,他是整整两个月“泥巴扫帚不离身”。他说我们是学美术的,要讲美;赃、乱、臭有什么美?我在这里教一天,这个教室和里面的人和事都在管的范围”,他也确实始终坚持教书又教人,从不马虎迁就。 周先生对教学工作极端负责。为了使同学尽快牢固地掌握动物雕塑技法,他对每个学生的每一件习作都认真辅导,边改边讲,由浅入深,举一反三,诲人不倦。每天迎来第一个进教室的同学总是周老师;每晚最后一个离开教室的还是周老师。每当同学进入梦乡时,他还在思考着明天的工作安排,他一心扑在教学上往往忘记了休息。他常说:“这么好的学生,我要对得起他们,能有机会付出点劳动是我的幸福”。 两个月很快过去了,我们同周老相处时身受的教益异常深刻,他的身教重于言教,教书又教人,他的严肃认真一丝不苟的工作态度和艰苦朴素的生活作风,为我们树立了很好的榜样。